|
如果问起近段时间我最亲近的“东西”是什么,毫无疑问,那应该是两面“墙”,一面是我办公室的,另一面是楼上会议室的,它们的共同特征有两个,陈旧斑驳和低矮逼仄。
每天早晨睁开眼,简单的洗漱之后,我与第一面墙的“缘分”就开始了。埋头写材料的我,专注处理公务的我,眼睛酸痛了,脖子提意见了,就会抬起头来,看它涂抹不均的泥灰和被岁月刻下的道道纹络,那些或深或浅的伤痕,似乎都在提醒我,人和墙,都会老去。
到了晚上,我与另一面墙的“亲昵”时光就到来了。我们之间的距离其实更近,只有不到一米的范围,屋顶漏雨的缘故,它的“皮肤”更差一些,呈现淡淡的黄色,甚至露出表皮下的红色砖体,就像年老的人裸裎出不甚雅观的筋骨,这边鼓起一块,那边凹进一块。
去年十月,我被调整分管办公室,一个我从来没有具体接触过的岗位和领域,虽然此话有失偏颇,毕竟身为单位人,不可能不接受“中枢机构”的管理与监督,只不过是分工不同罢了。众所周知,如果想做好办公室工作,会写、写好材料是首要的基本功,于是,我的难题就来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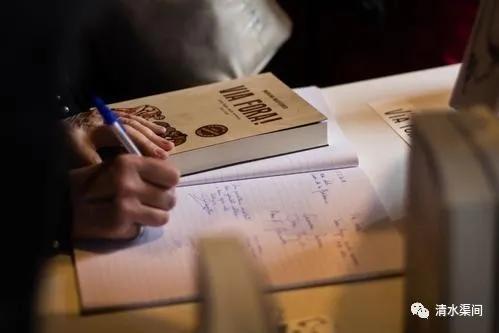
曾经听过不少议论:材料,是最严谨最规范的一种公文文体,有别于散文的“天马行空”,即便对于一个作家来说,能写好一篇惊世散文,未必就能写出一篇被大众或领导认可的材料。事实上,我的身边早有不少这样的例子。
朋友王某,郑大中文系高材生,学富五车,满腹经纶,堪称文史专家,原在一所高中教书,无意参加全市科级干部选拔,凭借深厚的文化素养,没料想一举拔得头筹,荣任某委副主任。适逢年终考核,一把手安排让他整理一个汇报材料,大跌眼镜的是竟收获了这样的结论:思路不着边际,内容空洞无物。很是让这位仁兄羞愧了好一阵子!
自此,就像得了“恐惧症”一般,遇到需要撰写整理的材料,不管是本部门的还是任务下派的,我是能躲则躲能避则避,实在推不过去了,就找出以前的总结或者报告“复制剪贴”炮制一通。总而言之,不求质量只求数量,反正已经有了。
关于写材料,我曾经闹过一个不大不小的“风波”。那是刚接手不久,上面要一个经验交流汇报,一稿要求压缩字数,二稿要求突出亮点,五稿、六稿要求全新视角、不泯同行,弄得我彻底懵了,“标准到底是什么?”,感觉有关部门是在故意拿人开涮,整日忙不得出的小屋简直就是桎梏我的牢房,那面破墙上的每个斑点和疤痕,似乎也变成了嘲笑的眼睛,最终使我怒不可遏,壮胆在电话里跟“老大”撂了挑子,“您另请高明吧,我实在干不了!”
“公文格式要求合法与统一,语体要求简明严谨,文字侧重朴实无华,总体来说,是在为单位(或)领导代言。你刚接触公文不久,写不好有急躁和畏难情绪,这很正常”。和蔼的“老大”,不仅没有责怪我的无礼,还专门找我谈了话,脸上的微笑,始终没有消失过。
“我看过你的多篇散文,有很强的文字功底,但文学作品是写作者个人感受的表达体现,这与公文的‘公为万民’有着本质区别。以后只要注意把握住行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、学会转换角色和身份,相信你一定会写得更好!”“你这段时间的材料,几乎不用我多做修改了,不出半年,你就可以出师了!”.....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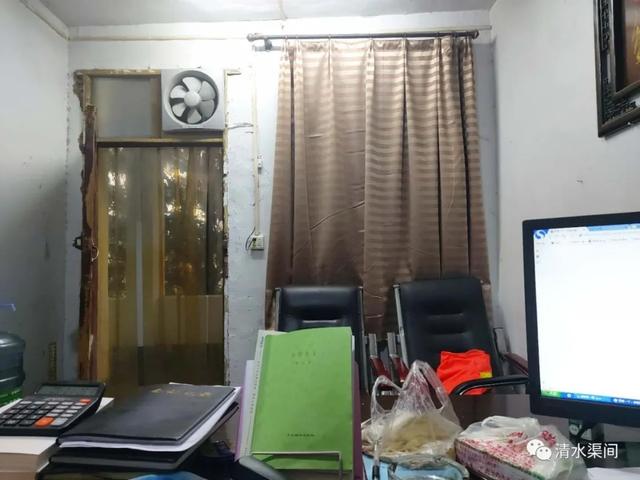
驭人之道,攻心为上。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罕见的全日制本科生,“老大”的履历可谓精彩。先是因为综合能力突出,被借调到市里某重量部门,后来一路拔擢主政一方,其才思敏健其谋略胆识,素为与之共事过的人津津乐道,有口皆碑。心结非结,只有想明白了,纠缠在心里的怨忿自然就消失了;心墙非墙,只有努力过了,矗立在心里的壁垒自然就瓦解了。
除夕前夕,突如其来的肺炎疫情,使得很多人回家的愿望变成了渴望,留守在单位,战斗在一线。他们中有初入职场的男孩女孩,也有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男女,他们的身份有干部、医生,也有许多无名的爱心人士和社会志愿者。他们用双肩担起了光荣的防控责任,他们用忠诚筑起了道道阻击病毒入侵的“人墙”。我在另一面会议室的“墙”下,在用手中的笔记录下会议内容的同时,也用手机记录下了部分瞬间感怀和所思:
“2月1日21:54,有时候我们日复一日地做着同一件事,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有朝一日不必再去做;我们经年累月地过着同一种生活,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过上另一种生活。2月2日22:08,但求心无愧,莫问为了谁;事了拂衣去,深藏功与名。2月27日22:51,雨沛春来早,衣食当可足。旌旗凌空舞,下有不眠人”......
最近的当属标记为(前天)3月2日“第38次调度会”的23:57分,当主要领导重申“疫情防控不能松懈,乡村振兴不能掉队”,连续签发了数个关于项目推进、农村改厕、植树造林、春耕备播等文件,群情激慨与心念闪动之下,我敲出了这样几行文字:“方寸斗室,别有洞天;一言既出,可令万千!”

作家张抗抗说,“大山是墙,人心是墙,除了墙之外的一切都是墙,可是这世上原本是没有墙的。”是的,所有的墙都是人为建设的,自己垒砌的,就像惧怕面对的所有困难,永远迈不出去的迟疑脚步,它们都是一面面看不见的墙,心墙既无,世界坦途。
此时此刻,我想的最多的是,疫情过去,我不想去桂林,也不想去成都,就想去看看为之奋斗着的这片土地,到底有多美——风景不在远方,它在我们甘愿留下的每个地方。因为我相信,脚下的大地喜欢接触我们的赤脚,田野的风渴望戏拂我们的头发。


|  |删帖申请|Archiver|手机版|小黑屋|掌上登封
( 豫ICP备20000995号-1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豫B2-20200172 )
|删帖申请|Archiver|手机版|小黑屋|掌上登封
( 豫ICP备20000995号-1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豫B2-20200172 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