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
作为一个闲余随便写点心情文字、聊以自娱的业余文学爱好者,我素来承认自己没有对任何一类学科任何一种思潮有过系统地、有计划的阅读和学习,以至于听到身边很多人侃侃而谈什么文学流派,大论特论某个大咖的写作风格,总是缄默闭口,不敢发声。
如果从在学校文学社蜡纸印刷发表第一首小诗算起,到现在开公众号想写就写自己喜欢的文字,我的“文学之路”不可谓不长。究其缘由,我想更多的原因之一是“需要”——性格内向,拙于口讷于言,看到陌生人就脸红,惶惶不安,不如埋在书本里遇见本我;还有另一个原因应该是“自保”——世界何其繁杂,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各种是非与陷阱,不如遁在文字里看长天,上高楼。
缺吃少穿的年代,拥有一本专门买给自己的书,绝对是一种奢望,所以跟大多数农民家庭的孩子一样,特别羡慕那些经济条件好的同学,因为他们总能带来连老师也没看过的“新书”。比如有着著名的“人最宝贵的是生命”片段的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,朗朗上口的《三字经》《唐诗三百首》,还有即使篇幅短小却道理深蕴的《故事会》,都曾是我无比艳羡的对象。由是千方百计去跟他们搞好关系,甚至讨好他们,只为能够借来读上几遍,玩味一番,即是困顿的日子里最大的幸福。
发现自己的浅薄和不足,是在升入初二的那一年。原以为每次都被老师看好、当作范文的我和我的作文,忽然遇到了一个强劲的“对手”:他是从县城转来的,听说父亲是乡里的主要领导,母亲在一所中学教书,自小便熟读经书,过目能诵,据老师点评,他的文章“用典合宜,龙头凤尾”。当时,我很纳闷,这是什么意思呢?后来渐渐明白,老师的评价原来是“主题鲜明,结构紧凑,引用得当,文字凝练”,比起自己那些流水账式的记事文和强拼硬凑的说明文(当时还没有学写议论文),实在是有着天壤之别!
赶上他,甚至超过他,一度成了我心头上最紧迫最重要的目标。琼瑶阿姨的《窗外》《在水一方》,拿来,正好可以提前探究一下少年难以诉说的懵懂情怀;梁羽生大叔的《萍踪侠影》《白发魔女》,拿来,刚好能够构造餍足一下男孩激荡飞扬的侠客之梦;博大瑰丽的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,拿来,恰好可以穿越触摸一下神奇旖旎的神仙界金陵城;晦涩难懂的《山海经》《道德经》,拿来,凑巧能够揣摩感知一下古圣先贤的妙想奇思。开卷有益的乐趣,非沉浸在其中的人,无以体会。
想让你的文字辞简意赅,要言不烦,建议多看古文书;想让你的笔下美轮美奂,风雨如画,不妨多看徐霞客;想让你的思想深邃厚重,意境幽远,建议多读王阳明;想让你的风格清新脱俗,欢快可亲,不妨多读纪伯伦......需要什么读什么,读什么补充什么,随性而至,随心而来,不知不觉中,无声无息地,你会慢慢发现,眼前的一切越来越美丽,天上的白云越来越轻盈——文章本天成,妙手偶得之;好书本无类,慧眼见人生。何必在意你读的是谁的书?还有什么必要争个你高我低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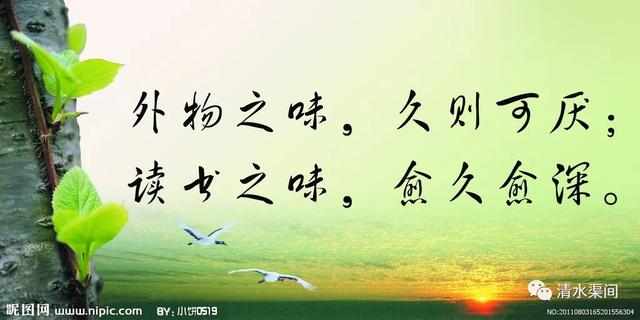
杂览胜于不览,有书幸于无书。作为普通上班族,每周或者每月花十几块甚至几十块钱买一本书,难免会觉得心疼不舍,也总在为是否“清空购物车”犹豫不定,暗自伤神。袁枚说,“书非借不能读也”,劝勉世人要好学读书,将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,把外界的压力变为前进的动力,讽刺那些只会藏书、吝书而不知爱书、读书的守书奴,赞美那些博览群书、潜心研究的学者大儒,对此,我深表认同。爱读书的人自然爱书如命,所以我要深深感谢曾经无私借书给我的同学或者朋友们,是你们让我一步步见识到了文字的魅力,领会到了世界的浩瀚,更让我一点点看清了生活的真相,明白了活着的意义。
唐代张潮说,“藏书不难,能看为难;看书不难,能读为难;读书不难,能用为难;能用不难,能记为难。”随着年岁的渐长,静多动少,一有空闲我就喜欢宅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,醉心于半生“搜罗”来的书海里不能自拔,自乐陶陶。有一个比喻,不知妥不妥帖:当你左图右史、经传子集前翻翻后抚抚的时候,那种被簇拥被环抱妙不可言的滋味,有如帝王出巡百州,更如山风拂过百合,这一刻对我来说,每一本书都是无价美玉,它的形式意义,早已超过了它所描述的所有内容。


|  |删帖申请|Archiver|手机版|小黑屋|掌上登封
( 豫ICP备20000995号-1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豫B2-20200172 )
|删帖申请|Archiver|手机版|小黑屋|掌上登封
( 豫ICP备20000995号-1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豫B2-20200172 )